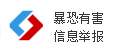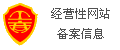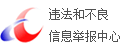|
周六的早晨,我去不远处的航院找茹,就是晖说的那个我的漂亮老乡。她住的宿舍是一幢极破旧的老楼,墙上已斑斑驳驳的。上了二楼,在她的寝室外敲了好半天的门,才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女生把门开了一条缝,我从门缝里看见了里面的凌乱。她问我找谁,我说出了茹的名字,她立刻说她不在。我正要离去,屋里传出茹的声音:“让他等会儿!”那女生有些尴尬地冲我笑笑,说:“没办法,来找她的人特别多!” 过了不到10分钟,茹出来了,我惊讶于她梳洗的速度。我们在她的校园里慢慢地走着,说着漫无边际的话,自始至终,她也没问我找她有什么事。后来她像想起什么似的说:“哎呀,我还有事呢!”于是我微笑着和她说再见,此时校园的广播里正放着配乐散文朗诵。她笑着说:“我不送你了,你听,是我做的广播节目,让我的声音陪你走到校门吧!”在茹好听的声音里,我离开了航院。 晚上临睡的时候,晖给我打电话,也没什么事,就是问候一下,因为她一整天没看见我的影儿。 那以后我再没去找过茹。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已是寒假,在家乡的小城。我们走在飘雪的街上,记得当年上中学时,每天的晚自习后我都送她回家,那些个晚上,或星月灿烂,或飘雨飞雪,不知不觉就走了过来。如今重走在当年的路上,却是情怀迥异。她不再是当年羞涩的小女生,大声地给我讲着她的大学生活,包括她的恋爱。而我始终微笑地静听着,像个善解人意的大哥哥。在她家楼前的路灯下,我们停住了脚步,她说:“谢谢你又一次送我!你回吧,我看着你走!”我转身疾行,走出很远回头望去,她仍站在那里,头顶的路灯迷朦闪烁,像许多正在模糊远去的往事。 春节后,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,小心地问我心情怎么样,我对她说很好,却忘了问候一下她,也忘了给她新年的祝福。开学后很久我才知道,在晖给我打电话的那些天,深爱她的外婆去世了。我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愧疚。 (三) 周六的晚上有球赛,中国对韩国,那时寝室里还没有电视,我们很早地来到电教室,可是里面已是人满为患。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校外找了个饭店,坐在大堂里边喝酒边看球赛。这之前晖非要跟来,我说:“你不是不喜欢足球吗?”可大伙起哄,只好带她去了。 大堂里还有一桌人和我们一样,也在边喝边看,看样子也是学生。看球的时候,晖安静地坐在我身边,完全不受我们热烈气氛的影响。后来中国队输了,大伙先是沉默再就是怒骂,骂来骂去的就骂到了韩国人身上,后来顺便把朝鲜族人也带了进去。正骂得兴起,忽然一个啤酒瓶凌空飞来,在桌上炸开了花。晖一声尖叫后,一瞬间全安静了,邻桌的几个人指着我们说:“骂人别牵扯太多,朝鲜人怎么了?”大家纷纷站起来,抄起了空酒瓶,我刚一伸手,晖忽然紧紧地拉住了我。此时局面已不可收拾,双方借着酒劲儿打在了一起。我想冲上去,可一看晖害怕的样子,便拉起她跑出了饭店,一直把她送进校门,可她哭着不让我去,我好说歹说才把她哄回去。 等我回到饭店,里面已空无一人,原来都被带到派出所去了。来到派出所,看见双方是两败俱伤。我和民警说尽了好话,并说我们是一起的,喝了酒闹点矛盾,没什么大事。民警们挺通情达理的,说:“看你们都是学生,态度也好,就不通知你们的学校了!”从派出所出来,我们再也无动手之意,双方互相看了看,各带伤员走了。 回去后发现晖还在校门那儿等我们,我悄悄对她说:“灰姑娘,别担心,什么事都没有!”她有些幽怨地瞪了我一眼。 说来也巧,一个月后我们和体校踢联谊赛,竟遇见了当初打架的那些人,原来他们是体校的。两队在球场上很文明,虽比赛激烈却都动作不大。最后踢成了平局。赛后双方一起去饭店庆祝,场面比球场上还热烈。这是真正的不打不相识,结果都成了好哥们儿。一年后毕业的时候,我们这群铁血男儿全都掉了泪。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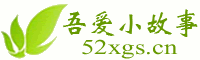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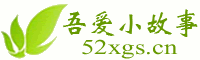
 主页 > 友情故事 >
主页 > 友情故事 >